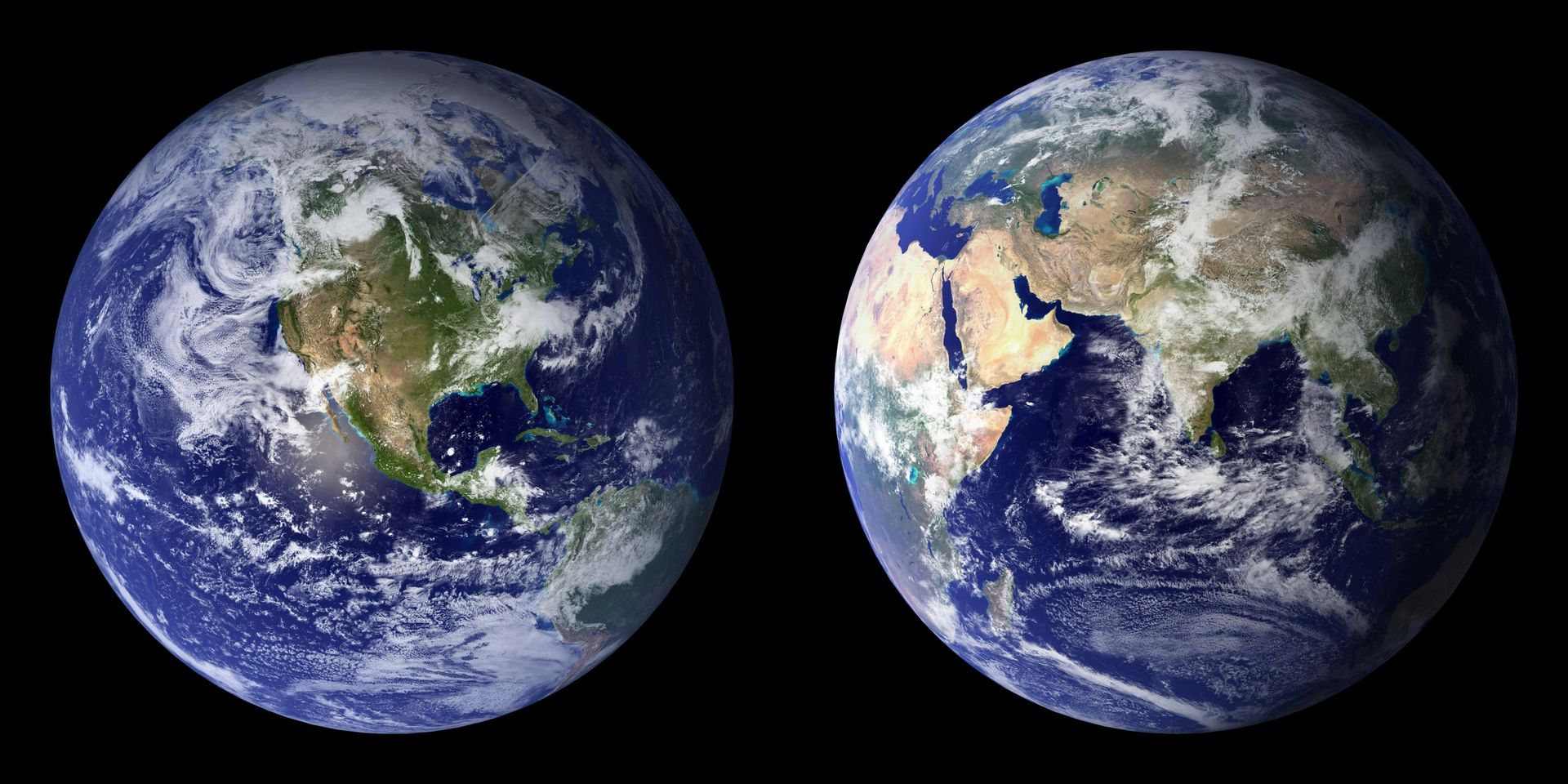憂鬱症:身心系統的失衡,以及重新校準的可能
作者|楊紹民 醫師|楊紹民心靈自然診所
一、憂鬱症的本質:它不只是一個情緒障礙,而是一個「系統問題」
臨床上,我常聽到類似的描述:
「我不是不想好起來,是身體跟不上。」
「我知道要休息,但大腦好像沒有煞車。」
這些陳述指出了一個核心觀點:
憂鬱症不是單一器官的疾病,而是整體系統的失衡。
我們已逐漸從「血清素不足」這種單一角度觀點移開,因為近年大量研究顯示,大腦的化學訊號不會孤立出問題。大腦、腸道、內分泌、自律神經、迷走神經、神經傳導物、免疫系統之間存在緊密的雙向軸線( brain–body axes,身體—大腦軸線 )。
這意味著:
- 壓力可能先影響睡眠
- 睡眠惡化會干擾前額葉與杏仁核的調節
- 杏仁核過抗引動自律神經失調
- 自律神經失調會帶出腸胃症狀
- 身體慢性發炎使大腦神經可塑性下降
- 大腦開始「偏向負向預測」
最後,我們看到的憂鬱症,其實是這些軸線功能長期偏移後的呈現。
如果從系統觀點看憂鬱症,那麼「情緒低落」只是一個表層現象,真正的核心,是生理節律已經無法自行回到平衡點。
二、情緒低潮與憂鬱症:差異不在「情緒強度」,而在「系統能否回彈」
在我的臨床經驗裡,真正能區分憂鬱症與一般低潮的標準,並非心情的好壞,而是:
一個人承受壓力後,是否還能恢復原本的生理節律與功能(function)。
1. 低潮,是可逆的
睡一覺、運動、談一場深度對話,都可能讓人回到原本的情緒曲線。
2. 憂鬱症,是生理反應「卡住」
各種身心調節機制失去了彈性,不再能自然回到基準線——就像一個被拉過頭的彈簧,失去自我修復的能力。
因此,臨床上更常觀察到的是 功能的變化 ,而非情緒本身。這也是國際臨床指南的共識:功能失衡才是關鍵切點。
舉例來說,我曾照護過許多高責任感的個體。他們不是突然崩潰,而是:
- 開始拖著身體完成日常
- 需要更多時間才能啟動
- 消耗比以往更多的心理能量
這些現象反映的不是「個性」,而是前額葉—基底核動機迴路( prefrontal cortex–basal ganglia circuit,前額葉皮質與基底核路徑 )的活性開始下降。
情緒低潮與憂鬱症之間的界線,從來不是意志力,而是神經生物學是否能自我回彈。
三、早期前兆:情緒還沒變差之前,身體已經開始在提醒
在臨床端,我經常看到患者的第一個症狀不是情緒,而是 身體日常節律破掉 。
這些前兆通常細微,卻具有高度預測性。以下以論述方式整理其機制與意義。
1. 睡眠的週期開始鬆動:這是壓力系統的第一個訊號
睡眠常常是最敏感的指標。
我觀察到許多人在憂鬱症發生前 1–3 個月,就開始出現:
- 清晨提早醒來
- 一晚醒來數次
- 睡醒仍像沒休息
這與 HPA 軸( hypothalamic–pituitary–adrenal axis,下視丘–腦下垂體–腎上腺軸 ,也就是壓力系統)過度活化有關。皮質醇在清晨自然上升,但當壓力調節失衡時,皮質醇曲線提前或過度升高,造成清晨早醒(Morris et al., 2014)。
在神經科學裡,這被視為一種「軸線提前啟動」的現象——身體比情緒更早覺察危險。
2. 認知開始變慢:不是個性變了,而是神經網路運算效率下降
許多人會描述:
「不是我不想做,是大腦像被黏住。」
這不是主觀感受,而是可以在功能性 MRI 上看到的:
前額葉皮質( PFC,prefrontal cortex,前額葉皮質
)與基底核( basal ganglia,基底核
)的連結下降。
這種認知遲緩( cognitive slowing,認知變慢 )很常發生在憂鬱症前驅期,與多巴胺反應降低有關。
它不會因為「打起精神」就消失,因為這條路徑的放電能力本身已經變弱了。
3. 情緒反應「閾值」下降:不是情緒變多,而是失去調節能力
憂鬱症的情緒問題,並非情緒本身,而是:
- 前額葉對情緒的抑制力下降
- 杏仁核(amygdala)對威脅訊號變得敏感
因此外界刺激不需要很大,就能引發劇烈的內在反應。
這並不是「變得脆弱」,而是 調節網路(regulatory network,情緒調節神經網路)功能下降 (Disner, 2011)。
4. 身體症狀增強:腦腸軸與自律神經一起被牽動
在憂鬱症前期,腸胃症狀的出現率非常高,包括:
- 腹瀉
- 脹氣
- 胃口變差
腦腸軸研究指出,腸道菌相與情緒調節高度相關(Foster & Neufeld, 2013)。當壓力與睡眠破壞腸道平衡,情緒迴路也會受到影響。
這不是「壓力大所以胃痛」的簡化版本,而是:
腸胃、免疫、自律神經與大腦是連在線上的一個系統。
四、大腦裡發生什麼:從神經迴路的角度理解憂鬱症
如果把憂鬱症看作一種「系統失衡」,那麼大腦裡的反應就非常清晰。
以下我會以論述方式整合三大重點: 壓力、神經可塑性、神經連結性。
1. 壓力系統(HPA 軸)無法關機:皮質醇讓大腦進入高耗能模式
當壓力長期存在,大腦的壓力軸線會從「即時反應」變成「長期上線」。
這會造成:
- 皮質醇升高
- 睡眠節律破壞
- 海馬迴(hippocampus)體積下降
- 情緒調節功能下降
(Sapolsky, 2015)
我常形容這像是一個永遠沒關機的警報器。大腦會因為長期處於警戒狀態,失去判斷「什麼是真正的危險」。
2. 神經可塑性下降:BDNF 降低使大腦無法切換模式
BDNF( brain-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,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 )就像大腦的養分。
當壓力、發炎或睡眠破壞神經可塑性時:
- 大腦形成新的正向迴路變得困難
- 負向迴路容易自動運作
- 情緒與動力恢復速度變慢
(Castrén, 2014)
因此,憂鬱症會是一段人容易覺得「被卡住」的時期。許多患者在症狀改善後仍感覺沒力氣,就是因為神經可塑性的恢復需要更長時間。
3. 神經網路連結下降:大腦的三大網路失去協調
研究指出,憂鬱症涉及三個主要網路的功能失調:
- 預設模式網路 DMN( Default Mode Network,預設模式網路 )過度活化:使人不斷反芻過去
- 顯著性網路 SN( Salience Network,顯著性網路 )敏感度上升:過度放大負面刺激
- 執行控制網路 ECN( Executive Control Network,執行控制網路 )活性下降:失去行動力與調節能力
(Mulders, 2015)
這是為什麼:
- 無法停止負面思考
- 即便知道不合理也拉不回來
- 無法啟動行動
這不是個性,而是三套大腦系統在不同步運作。
五、壓力 × 發炎 × 自律神經:憂鬱症背後的三重失衡系統
從臨床角度來看,憂鬱症通常不是突然發生,而是三個系統在一段時間內逐步偏離平衡:
- 壓力系統(HPA 軸)
- 免疫與發炎系統
- 自律神經系統(autonomic nervous system)
這三個系統彼此互相影響,形成一個循環,使得情緒狀態難以在短時間內回復。
1. 壓力系統:HPA 軸長期啟動後,調節能力下降
壓力軸線的啟動是自然反應,但當壓力維持過久,HPA 軸便不再敏銳。我常將這個機制比喻為:
「門鈴按太多次後,鈴聲會變得失真,但警報系統卻仍在高頻放電。」
臨床上,我看到許多患者的生活節奏早已超過自己能承受的上限,而身體的補償機制已經無法維持平衡。這正是為什麼:
- 情緒波動變大
- 睡眠變差、早醒
- 心跳加快
- 即便休息也恢復有限
這類現象背後不是「抗壓性差」,而是壓力軸線的調節能力下降(Sapolsky, 2015)。
2. 微發炎狀態:免疫系統影響情緒的速度比我們想像得更快
近十年研究逐漸證實,發炎反應與情緒失衡之間存在高度相關性。許多憂鬱症患者在抽血時可看到以下指標略為上升:
- IL-6(interleukin-6,介白質-6)
- TNF-α(tumor necrosis factor alpha,腫瘤壞死因子 α)
- CRP(C-reactive protein,C 反應蛋白)
即便處於「低度發炎」的狀態,也會明顯影響情緒調節與神經可塑性(Miller & Raison, 2016)。
這不是心理問題,而是生理訊號。
在臨床中,我觀察到當身體處於發炎狀態時,以下症狀會加劇:
- 倦怠
- 情緒陰影感
- 反芻思考
- 對壓力敏感
當我們協助病人穩定免疫反應時,情緒並非立即改善,但「整體彈性」會提升——就像將一個過度拉緊的系統稍微放鬆。
3. 自律神經失衡:交感神經處於高張狀態
自律神經是整個身心調節的樞紐。
憂鬱症患者常見:
- HRV 降低( heart rate variability,心律變異度 變低)
- 交感神經活性升高
- 副交感神經反應變弱
(Kemp et al., 2010)
這會導致:
- 腸胃蠕動變慢或過快
- 胸悶、心悸
- 呼吸淺
- 身體疲勞
- 睡前無法放鬆
這些現象不是「想太多」造成的,而是交感神經長期佔據主導地位,使身體無法進入修復狀態。
六、腦腸軸、免疫、荷爾蒙:情緒如何透過全身被牽動?
1. 腦腸軸:腸胃不適並不是偶然,而是生理 feedback
近年研究顯示,腸道菌相、腸黏膜完整性與情緒之間具有明顯關聯(Foster & Neufeld, 2013)。
腦腸軸( gut–brain axis,腦–腸軸線 )透過迷走神經與免疫反應,直接影響:
- 血清素前驅物代謝
- 發炎反應
- 自律神經穩定度
這解釋了為什麼許多患者在憂鬱症前期,腸胃症狀會成為最早的訊號。
在臨床上,有些患者在情緒尚未明顯低落前,就已開始出現:
- 腹瀉、便秘交替
- 飽足感下降
- 胃口紊亂
這些都是系統正在失衡的前兆,而不是「腸胃比較敏感」那麼簡單。
2. 荷爾蒙波動:生理變動會直接牽動情緒中樞
尤其在女性族群中:
- 產後荷爾蒙急降
- 多囊性卵巢症候群(PCOS)
- 甲狀腺功能異常
- 更年期
這些因素皆會透過下視丘—垂體—腎上腺軸(HPA 軸)與神經傳導系統,影響:
- 情緒
- 動力
- 睡眠
- 焦慮
在臨床觀察裡,這些荷爾蒙相關因素常與憂鬱症狀一起波動,因此理解「生理 × 情緒」的交互作用非常重要。
七、憂鬱症的四個階段:臨床觀察下的進程
雖然每位患者的曲線不同,但憂鬱症發展通常有可辨識的模式。
1. 前驅期(最適合介入)
這是大多數人不會察覺、但最值得注意的階段。症狀包括:
- 睡眠紊亂
- 動力下降
- 腸胃變差
- 認知速度變慢
在這個階段介入,效果通常最好,因為神經可塑性仍具有調整空間。
2. 急性期(功能明顯下降)
特點是情緒與功能同時受到影響:
- 明顯快樂感缺乏( Anhedonia,快感缺乏 )
- 對日常活動失去興趣
- 無力感、失能感
這不是心理意願問題,而是神經迴路能量已經顯著下降。
3. 恢復期(神經可塑性開始回升)
臨床上,患者通常會說:「好像慢慢恢復,但很怕再掉回去。」
這是神經可塑性逐步恢復的階段,但仍需要:
- 規律作息
- 壓力調節
- 自律神經支持
- 避免過早負荷
否則很容易重新倒退。
4. 維持期(防止復發的重要階段)
憂鬱症的復發率不低,其關鍵在於維持期是否足夠穩定。
維持期的重點是:
- 保持睡眠節律
- 維持身心負荷的平衡
- 強化行為韌性(behavioral resilience,行為上的彈性與穩定)
- 避免情緒壓抑累積太久
這個階段常被忽略,但對長期穩定非常重要。
八、治療策略:多軸線整合,而非單一方式
在臨床實務中,最有效的憂鬱症治療通常不是靠單一方法,而是透過 多軸線整合 :
- 生物性治療(由醫師評估是否需要藥物或營養補充劑)
- 心理治療(認知行為取向、情緒覺察、創傷治療)
- 自律神經調節(呼吸、冥想、節律訓練等)
- 生活型態介入(睡眠、運動、飲食等)
- 非藥物支持(依法規:例如 rTMS 等治療方法,由醫師評估適應症與安全性)
不同方法各有其介入點,而真正治療的是「整體系統重新找回節律」。
九、rTMS:在大腦科學中的定位
rTMS(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,重複經顱磁刺激 )是一項治療方法,使用磁場脈衝刺激特定腦區。
在科學研究裡,rTMS 的討論並不是著重在「治療情緒」,而是在:
調節神經網路的活性,使大腦較容易回到穩定節律與連結性。
根據功能性 MRI 研究,憂鬱症患者的前額葉—邊緣系統連結常偏弱,這使得情緒調節能力下降,而壓力訊號容易放大。
rTMS 的研究討論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面向:
1. 神經可塑性(Neuroplasticity)的促發
rTMS 能夠改變神經元放電模式,產生類似長期增強與長期抑制的效應( LTP/LTD-like effects,類長期增強/長期抑制效應 )。這在生理學上意味著神經迴路的「學習能力」被重新啟動。
參考研究:
- Lefaucheur et al., Clin Neurophysiol , 2020 – 國際共識指引。
- Hoogendam et al., Front Psychiatry , 2010。
2. 前額葉調控能力的強化(Executive Control Network)
許多研究指出,左側背外側前額葉( DLPFC,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,背外側前額葉皮質 )活性低於平均會影響:
- 壓力調節
- 行動啟動
- 動力與目標感
- 抑制負面預測
rTMS 的刺激位置正是這個區域。科學上並非「直接改變情緒」,而是:
提升前額葉的調節能力,使其重新有力氣穩定整體網路。
3. 提升網路同步性(Network Connectivity)
2022 年一篇大型連續影像研究指出,憂鬱症與網路同步性下降有關,包括:
- DMN 過度同步
- ECN 與 DMN 失去平衡
- ACC(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,前扣帶迴皮質 )訊號變弱
rTMS 的科學討論在於提升特定網路的同步,使整體神經節律回到更適應的狀態。
參考研究:Williams et al., Nat Hum Behav , 2022。
需要強調的是: rTMS 並不是萬靈丹,而是由醫師評估後,能在整合照護中提供的其中一項支持工具。其效果並非單獨發生,而是在精神醫療、心理治療、生活介入等多軸線並行時,對大腦調節提供額外助力。
十、生活方式介入:科學支持的十項大腦節律調節方法
從腦神經觀點,生活方式不是附屬性建議,而是核心干預。因為神經可塑性、壓力軸線、自律神經,全都「依賴生活節律」運作。
我會將生活方式介入視為 神經可塑性營養素 ——不是指營養補充品,而是讓神經元有能力重新連結的日常條件。
下面這十項方法,是具有研究支持、且臨床上最常帶來改善的習慣:
1. 規律睡眠:大腦修復的必要條件
睡眠是修復前額葉與海馬迴的關鍵。睡眠不足會加劇:
- 情緒擺盪
- 反芻
- 壓力感
- 認知疲乏
研究指出,規律的睡眠節律能提升情緒穩定度(Walker, 2017)。
2. 早晨光照(10–20 分鐘)
早晨光照能調整:
- 生理時鐘(circadian rhythm,晝夜節律)
- 皮質醇節律
- 血清素前驅物合成
對自律神經與情緒皆有益處。
3. 中低強度運動(以走路為例)
運動能提升 BDNF。BDNF 是大腦連結與彈性的核心。
不需要強度很高, 持續性最重要 。
Aerobic training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BDNF(有氧運動與 BDNF 升高有關)(Szuhany et al., 2015,系統性回顧與統合分析)。
4. 減少多工行為
多工會使前額葉耗能增加,情緒敏感與疲憊感會更加明顯。減少多工,有助於恢復專注與降低認知負荷。
5. 迷走神經刺激
例如:
- 延長吐氣的呼吸
- 腹式呼吸
- 身體掃描
- 靜態拉伸
迷走神經(vagus nerve)活性上升代表副交感神經與修復能力增加。
6. 腸胃照護
飲食變動會影響:
- 腸道菌相
- 發炎反應
- 神經傳導物質合成
腦腸軸的穩定度直接反映在情緒彈性上。
7. 行為啟動(Behavioral Activation)
行為啟動是一種認知行為心理治療中的一種技術,強調「先行動,再等待情緒跟上」。科學顯示,行為啟動能有效改善動力迴路。
從「可完成的小行為」開始,而不是等待「有動力」才行動,有助於重啟前額葉與基底核路徑。
8. 降低資訊刺激
資訊量大 → 壓力軸線啟動 → 注意力下降 → 焦慮上升。
限制曝露量(例如減少過度滑手機、追逐大量新聞)有助於降低神經耗能。
9. 社會支持(但不是情感依賴)
有效的社會支持,並不是不停地勸說或給建議,而是透過「共調節」( co-regulation,共同調節 )穩定神經系統。
這是目前神經生物學對人際支持的理解:安全、穩定的關係,可以降低杏仁核威脅反應、提升前額葉調節。
10. 慢性壓力管理(建立可維持的節律)
慢性壓力才是 HPA 軸失衡的主因。
找出能在日常中持續實施的「輕量調節」方式,遠比偶爾的重大改變更有效。例如固定的散步時間、睡前固定的放鬆儀式等。
十一、為什麼憂鬱症會反覆?(大腦預測模式DNM的觀點)
許多人在症狀改善後仍有擔憂:
「會不會又再度掉回去?」
從神經科學來看,這個擔憂值得被理解。
憂鬱症的復發率較高,關鍵原因不是「心理脆弱」,而是:
1. 大腦仍習慣走舊迴路(Negative Prediction Bias)
大腦偏向預測負面訊息,是因為:
- 預設模式網路(DMN)活動上升
- ACC 與 PFC 調節能力還未完全恢復
- 神經可塑性仍在重建
2. 睡眠、壓力、自律神經三者中,只要一個再次偏移,就容易觸發舊迴路
例如:
- 幾天睡不好
- 工作壓力突然增加
- 身體慢性發炎上升
這些都能讓神經系統回到舊模式。
3. 恢復期「看起來好了」,但神經可塑性其實還沒完全修復
臨床上最常見的是:病人覺得自己「差不多恢復」,便回到高壓、快節奏生活,結果迴路能量不夠,導致症狀重新出現。
4. 行為韌性(Behavioral Resilience)需要時間累積
行為習慣不是立即有感,但會在長期成為抵抗復發的關鍵。穩定的生活節律與行為模式,是神經系統維持平衡的重要基礎。
十二、親友如何支持:不是安慰,而是降低神經威脅訊號
在院內最常看到的誤解之一,是親友急著給建議:
- 「你要加油」
- 「不要想太多」
- 「找事情做」
這些話之所以無效,是因為:
憂鬱症不是思考問題,而是神經調節能力下降。
親友真正能提供的,是「降低威脅感」的環境,包括:
- 穩定的陪伴,而不是頻繁地評價或要求
- 開放、不急著解釋或分析,讓對方有表達空間
- 簡單、明確、不帶額外期待的支持訊息
- 適度協助日常節律(例如一起吃飯、散步)
這類行為能降低杏仁核的敏感度,提升前額葉調節,從神經層面支持恢復。
參考文獻
- Duman RS, Aghajanian GK. Synaptic dysfunction in depression: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s. Science. 2012.
- Moncrieff J, et al. The serotonin theory of depression: a systematic umbrella review. Mol Psychiatry. 2022.
- Treadway MT, Zald DH. Reconsidering anhedonia in depression. Psychol Rev. 2011.
- Simon GE, et al. Depression and medical symptoms. N Engl J Med. 2013.
- Morris MC, Rao U. Cortisol awakening response in depression. Psychoneuroendocrinology. 2014.
- Pizzagalli DA. Depression, stress, and anhedonia: basal ganglia dysfunction. Curr Opin Psychol. 2014.
- Disner SG, et al. Neural mechanisms of the cognitive model of depression. Nat Rev Neurosci. 2011.
- Sapolsky RM. Stress and the brain. Nat Rev Neurosci. 2015.
- Castrén E. Neurotrophic factors and depression. Curr Opin Pharmacol. 2014.
- Mulders PC, et al. Resting-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major depression. Neurosci Biobehav Rev. 2015.
- Miller AH, Raison CL. The role of inflammation in depression. Nat Rev Immunol. 2016.
- Kemp AH, Quintana DS.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rt rate variability, emotion regulation, and depression. Biol Psychiatry. 2010.
- Foster JA, McVey Neufeld KA. Gut-brain axis: how the microbiome influences anxiety and depression. Trends Neurosci. 2013.
- Szuhany KL, Bugatti M, Otto MW. A meta-analytic review of the effects of exercise on brain-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. Neurosci Biobehav Rev. 2015.
- Williams LM, et al. Mapping the neural circuits of depression. Nat Hum Behav. 2022.
- Lefaucheur J-P, et al. Evidence-based guidelines on the therapeutic use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(rTMS). Clin Neurophysiol. 2020.
- Hoogendam JM, Ramakers GMJ, Di Lazzaro V. Physiology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of the human brain. Front Psychiatry. 2010.
- Walker MP. Why We Sleep: Unlocking the Power of Sleep and Dreams. Scribner; 2017.